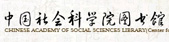区域合作
站内搜索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区域合作政策的思考
作者:刘均胜 来源::《世界区域化发展与模式》 时间:2004-08-10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实际上,如果从具体一国发展的角度看,则凸现出具体国家如何看待这两种潮流背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如何定位这两种潮流对本国发展影响等问题。其中,最重要且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对这两种潮流进行扬长避短的加以利用并优化本国发展战略及政策。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十年内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1]。笔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全球化将对中国的金融开放和能源供给提出挑战,中国应该制定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战略和政策,在为亚太地区自由、开放和共同繁荣的远景目标[2]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协调的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
尽管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的提法、影响等有很大的争论,但主流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认同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实质目前,较为普遍的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贸易和投资开放的行列,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加速了,国际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民族、地方的限制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整合。
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表现是贸易的国际化、生产经营跨国化和金融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主要表现是,近20年以来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其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生产增长率。生产经营跨国化的主要表现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实现生产经营的跨国化和生产一体化。金融的全球化是指由于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电子、电讯技术的发展,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金融在一体化层次上向更高层次迈进。
贸易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先导,实现了产品交换阶段的国际经济联系;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力量,体现了生产阶段的国际经济联系;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和驱动力,从要素配置阶段体现了国际经济联系。三者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有机构成,共同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世界经济生产的形式和实质: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3],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体系的建立和经济制度(规则)的渐趋统一。
(二)经济全球化中的政治经济学客观地说,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属于实证性的范畴,但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全球化的制度(规则)基础,则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属于规范性 的范畴。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不但是一个结构性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4],但是后者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所谓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性过程是指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就是前面归纳的贸易国际化、生产跨国经营和金融全球化。而制度转型过程则是指伴随结构过程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大改变,突出的表现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和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又开始循环的过程。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包括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经济全球化下,资本运动不但取决于货币资本及时转变为职能资本和商品资本及时实现价值增殖,而且关键性地取决于生产资本在全球内的扩大再生产。发达国家利用其市场经济原发性、资本规模和发展程度、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获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没有副作用,而只是强调发达国家更善于将经济全球化累计的矛盾向外转移。在资本逐利性使发达国家经济的全球化负面矛盾高度累计和急于向外转移时,经济全球化过程就可能会完全逆转。根据霸权周期理论[5],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周期:每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会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金融和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全球规模危机的爆发;危机使旧霸权国家与以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霸权国家与以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如果考察长期资本主义周期,还可以发现经济的周期运动主要由两个完全相反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保护的力量和释放市场的力量[6]。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由保护社会力量转向为释放市场力量的重要转折过程。这一过程以金融自由化为肇始,以20世纪90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7]为顶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因为发展中国家受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资本规模小、技术落后、作为国际经济秩序适应者等不利方面的限制,经济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负面效应。理论上,巴兰在《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发达国家的落后根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通过攫取大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创造加速发展条件,另一方面通过破坏性竞争摧垮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等著作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从宗主国到外围的扩张过程。伊曼纽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论证了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机制来不平等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伯克特在《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中指出,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的不平衡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从而妨碍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及其政策由它们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决定。[8]
从现实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纷纷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实践,虽然取得了相对的进步,但大多数爆发过严重的金融危机,陷入“金融压抑——自由化——金融危机”的怪圈。从20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1997-98亚洲金融危机,从债务危机后拉美经济的停滞到亚洲金融危机后仍没走出经济动荡的印度尼西亚,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主要在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爆发,并且危机的成本十分高昂。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国际化和生产经营跨国化阶段或者发展中国家参与贸易国际化和生产经营化层面的经济全球化活动,发展中国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在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全球化阶段或者发展中国家过早放松金融管制,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遭受巨大的损失。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在表面上是金融市场上投机资本对钉住型汇率制的冲击,背后则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同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9]仅就金融层面的问题来看,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国家理论[10],霸权国家通过金融全球化向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输出国际短期资本,新兴市场国家在获得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因输入了霸权国家的通货膨胀而导致本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最后在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下爆发金融危机。[11]
二、经济区域化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
(一)经济区域化的总体发展阶段从时间上看,经济区域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下半期;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开始,9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目前正向更深入层次发展。这两个阶段最重要的区别是,第一阶段形成的区域化组织基本上是封闭的,而第二阶段形成的区域化组织大都奉行开放性的地区主义。[14]目前学术界一般将第一阶段的经济区域化称为旧区域主义,而将第二阶段的经济区域化称为新区域主义。[15]
(二)新区域主义的特点新区域主义下的区域合作具有如下特征[16]:
1.合作的范围突破了区域或地缘因素的限制,跨洋越洲的次区域合作不断出现。基于地理位置的约束可以将次区域合作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两种类型(natural and unnatural)[17]。在传统的经济合作理论中,几乎不考虑运输成本,只是从静态的角度比较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导致的福利变化。在新贸易理论中,运输成本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18]。在近来的经济合作文献中,使用引力模型[19]来分析经济合作被广泛接受,其中由距离导致的运输成本被解释为涵盖风俗习惯、语言、价值观念等的一个多维范畴。
2.合作的主要内容除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外,还包括资本流动、服务贸易和敏感性产业的地区合作。更进一步,合作的内容扩展到社会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安全、环境、制止跨国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20]。表面上看,这些领域的合作目的取向不同于传统单一的经济合作范畴,但实际上亚太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是主要地受制于经济关系[21],其合作上不对称性导致多样性的合作形式。
3.合作的模式主要有契约型和非契约型两种,其行为主体可以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其具体形式可以介乎于法律形式、论坛形式等多种模式。灵活的合作模式可以充分挖掘潜在的合作好处,避免合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便于突破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还引起学者们对以往合作类型的划分进行了思考,通过比较优惠贸易安排(PTA)、自由贸易区(FTA)和关税同盟(CU)等区域合作形式,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如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关税同盟,发达国家则更倾向于优惠贸易安排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的合作[22]。
4.合作在意识方面注意避免“以邻为壑”现象的出现,不但重视内部的开放,还重视对外部的开放。“开放的地区主义”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突出标志,传统区域合作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征不断弱化,如何妥善处理成员与非成员之间的歧视性问题从合作的一开始就被广泛关注。现有的理论模型意识到合作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通过考察初始合作条件,论证了内向、封闭的次区域合作和外向、增进整体福利水平的次区域合作都有可能发生。
5.合作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南北型的合作格局不断涌现。过去的产品竞争已经让位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规则竞争,它决定了一国参与全球化获得好处和遭受损失的大小[23]。发展中国家在增强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合作的制度性建设,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经济规则的制定。
(三)新区域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旧的或传统的区域合作理论中,对区域合作的福利收益主要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的核心是通过大市场理论和竞争激化理论强调由于规模经济导致的区域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24]然而,当我们考察新区域主义的合作时,会发现大量南北型、跨洲型区域合作的出现,并不能很好地用传统的区域合作理论来解释。笔者认为,在新区域主义的合作中,不同类型的参与国在目标函数类型上存在差别,但其中的互补性构成合作的基础。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不同类型的参与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者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贸易战中的报复能力和谈判能力上的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参与新区域主义区域合作的目标是追求超越经济收益之外的非经济收益,具体说主要包括:通过提高贸易报复能力及整体谈判能力实现在同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中获胜;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增强区域内规则制定的能力;获得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主导权地位;取得单方支付。[25]如美国最初联合加、墨两国成立NAFTA,主要是为了增强报复和谈判能力以制衡欧共体一体化进程所导致的“欧洲壁垒”。1993年美国将原来定于在西雅图召开的APEC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时加快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在此之前国会刚好通过NAFTA议案,克林顿政府导演的这部“三步曲”向欧盟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如果欧盟不努力解决农产品等敏感问题以结束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则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自由化的谈判。[26]在1996年的信息技术协定(ITA)中,美国利用NAFTA和APEC最终使基础电信服务谈判纳入到WTO框架中[27]。这是美国通过区域合作影响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两个实例。在实现政治目标上,美国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考虑根据安第斯组织五国(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在民主制度、打击恐怖主义和缉毒合作程度的差异实行“双轨道”战略。欧盟则将民主化程度作为接纳东欧国家的一个先决条件。巴西尽管不是发达国家,但作为地区大国,在增强区域内规则制定上,巴西通过主导南方共同市场来挑战美国在美洲自由贸易区中的主导地位。巴西提出南方共同市场与安第斯条约组织应首先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然后所有南美国家在与NAFTA进行谈判。总之,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对美国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本质上是一项对外政策,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28]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新区域主义区域合作的目标更多的是以获得市场准入机会为代表的经济利益,但不排除非传统经济收益。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参与新区域主义合作的收益主要包括市场准入、保持改革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信号显示、提供保险、增强谈判能力以及建立协调机制。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外部市场依存度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和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得自市场准入的贸易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墨西哥在劳动密集性产品上具有优势,为了扩大出口,墨西哥通过对美国谈判上的让步或“单方支付”达成NAFTA协议以进入美国市场。在保持改革时间上的连续性上,仍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墨西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防止因国内选举导致改革搁浅,政府通过加入NAFTA实现了对现有改革路径的锁定。信号显示就是通过加入区域合作组织向外界投资者表明贸易开放、经济状况良好、政府透明等以吸引外资的流入。保险就是区域合作可以为成员提供防范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通过减少不确定性而增加成员的福利。增强谈判能力最好的例子是东南亚国家通过建立东盟而实现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话,从而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29]建立协调机制的解释是将那些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人组织起来,使其能协调行动。研究国际贸易历史可以发现,受益于自由贸易的主体一般都是分散的、具体获益不高的消费者,而在贸易中受损害的一般是集中、损失利益较多的生产者。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组织较好的小团体往往能战胜组织分散的大团体。这样,政策制定者常常在工会、生产者团体的压力下不顾自由贸易的社会福利改善而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方面的例子是日本政府被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俘获”而在对外政策上摇摆,如政府对农林水产部门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等。[30]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压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近年来连续保持快速增长,目前正以“世界工厂”和和平崛起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作为世界力量的一极[31],在不同时期和阶段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之间必然存在着积极抑或消极的互动,目前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作为两个突出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一)以石油为主凸现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石油供需矛盾的复杂性在于该矛盾出现的时期同世界能源市场的结构变化重叠在一起。一方面,中国通过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政府的公共投资保持了近年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与美国共同成为带动世界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据统计,2003年日本对中国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32%,韩国相应数字为36%,特别是日本其内需的增幅仅为1.5%。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完全摆脱高增长、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迅速增加。原油在1996年进口超过出口,石油制品在1990——1996年期间进口超过出口。实际上,从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如若按GNP保持8%—9%计算,2004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3%。据预测,未来2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石油对外依存度加大(见表1)。
表1中国未来石油供需平衡表(单位:亿吨)
| 年份 | 2000 | 2005 | 2010 | 2015 | 2020 |
| 需求量 | 2.3 | 2.8 | 3.4 | 3.98 | 4.84 |
| 自产量 | 1.63 | 1.8 | 1.95 | 1.9 | 1.85 |
| 缺口量 | 0.67 | 1.0 | 1.45 | 2.08 | 3.0 |
| 对外依存度 | 29.1% | 35.7% | 42.6% | 52.3% | 62.0% |
资料来源:单卫国:“中国石油:事关战略安全”,《世界知识》,2002年第21期。
另一方面,世界石油市场出现结构变化:在需求结构上亚太地区成为新的需求中心,占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量的90%;在供应结构上,除中东仍保持传统出口地位外,俄罗斯、中亚和西非成为新的供应地区,而老产区(北海、美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产量不断下降。英国经济学情报社首席经济师佩礼认为:“两类国家不得不对世界市场上的石油进行争夺。一方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它们、、、、、、;另一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它们、、、、、、”[32]
根据前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生产跨国化和金融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当前的世界石油地缘政治使中国难于获得足够的海外石油份额,这样中国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安全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实际上,战略家已经注意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决定市场,而资源却决定生产;一国的实力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总量,而决定于该国可绝对控制并能稳定地获取世界资源的总量、、、、、、[33]尼克松说,资源是西方政治的关键。[34]
(二)以汇率政策为主凸现金融安全问题2003年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焦点,实际上,在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背后涉及两个问题:1)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实现人民币升值;2)完全放开资本帐户,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如果根据前面对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同金融危机关系的分析,那么人民币升值问题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反映了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摩擦和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
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性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入WTO后以国际制造业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向中国转移,并且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域已经从原料、加工行业转向设备制造。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又刺激了对外出口的增加和商品贸易顺差的增大。由此,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根据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的报告,美国对中国的商品逆差增加了20%,达到创记录的1240亿美元。这一现象引起美国制定者的关注,被认为加重了美国当前经济复苏下的失业问题和侵蚀了对美国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制造业。[35]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生产商的竞争优势,美国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要求中国货币当局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以使人民币升值。
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不仅有贸易方面的考虑,还有金融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在东亚美元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变动对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大幅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36]亚洲金融危机后,尽管许多经济体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但近年来的汇率实证分析表明,这些经济体有向危机前的钉住汇率制回归的倾向。[37]东亚经济体为了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防止本币升值而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并被迫干预市场。这导致了东亚出口安全资产进口风险资产的特殊资本流动结构,即东亚国家所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投资美国国债等安全性、流通性高但收益率低的资产,与此同时,区内所需资金主要以较高成本从国际市场获得。[38]这种不对称的资本流动结构为美国的双赤字提供了大量的融资,对美国来说,保持这种资本流动的关键是使东亚各经济体对美国经济有信心,其次通过阶段性的美元贬值来使债务缩水。
对中国来说,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符合我国当前国情;逐步放松资本账户外汇管制,最终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应该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对于先行的人民币汇率,考虑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整个区域货币合作情况,保持当前的汇率稳定是最优选择。[39]如果从国际标准的货币自由兑换条件来看[40],在当前情况下使人民币升值或者过快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我国将面临金融安全问题。首先,扣除固定资本投资和国际原材料上涨因素,我国的实际消费物价指数表明还存在通货紧缩,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实质性增长;其次,考虑到当前局部经济过热,我国还存在制度上和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41];再次,国内金融体系在不良资产、资本充足率、赢利水平和资本市场发展上仍存在许多不足;最后,金融监管手段落后。[42]
四、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战略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也日趋加强。笔者认为,思考我国参与区域合作的战略政策应该建立在总体把握经济全球化规律、透彻认识中国面临的压力、明确区域合作的目标和手段的基础之上。
(一)总体判断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国际化、生产跨国化阶段或参与贸易、生产层面的经济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好处。在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全球化阶段,发展中国家过早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则有陷入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两个重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能否稳定地获得世界资源(对中国来说是石油的稳定供给)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障,而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避免外部冲击的金融政策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的关键。
(三)基本思路树立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积极推进地区繁荣的大国形象。中国应该采取务实的区域合作战略政策,最大程度地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利用区域合作的政策时间连续性、信号显示等机制,使美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要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43],使东亚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的发展会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开放和繁荣[44]。利用区域合作的内部规则制定和对外部规则的影响,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能源、金融约束降到合理的范围内。
(四)战略政策取向
区域能源合作政策取向
1、参与中亚和东北亚能源合作,成为连接石油供给和需求市场的中间环节。横贯北非的马格里布——波斯湾——里海——外高加索——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理上形成了世界石油富集地带,这里蕴藏着世界石油的65%和天然气的73%。[45]该地带被称为“世界能源的供应心脏地带”,围绕该地带形成两大能源需求圈[46],可具体归结为北美、欧洲和亚太的能源需求大三角。中国处于中亚里海俄罗斯石油供应市场和亚太石油需求市场的路桥国家地位。通过能源合作,一方面缓解我国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形成对中亚里海和俄罗斯的稳定亚太能源需求市场。加强能源贸易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通过解除管制、开放能源市场能够提高效率和减少成本,从而实现能源供需的最优均衡。特别是,要重视新能源安全概念中通过私人资本的介入来保证能源安全的思想[47]。
2、通过开发能源的功能性金融合作,整合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为建立新型的区域主义奠定基础。从东亚地区存在的多样化地区主义和合作层次来看,目前东亚没有形成统一的地区主义,而现有的地区化实际上是具有竞争性的放大的民族主义地区化[48]。这种民族主义为实质的地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于具有地区认同的统一地区主义产生危害[49]。开发能源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可以为实现从民族主义的地区化到以区域认同的新型区域化做出贡献。建立区域性的油气供给网是一个区域性的系统工程,金融合作不但可以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而且可以发挥其组织、协调的作用为日后能源制度化合作提供基础,这样可以突破目前基于国别油气供需体系的局限。
区域金融合作政策取向
1、通过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来扩大区域内部需求,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容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庞大生产能力,目前较为可行的是扩大亚太地区的内部需求市场,以缓解出口集中美国市场的压力。增强亚太地区的内部需求能力,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合作来改造东亚过去在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上不利扩大区域内部贸易和增加区域内部需求的制约因素。[50]具体措施包括:[51]
——建立促进投资便利化的机构,刺激区域内各类资本流动的增长;
——建立地区贸易结算体系和汇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
——建立区域性的投资开发机构,通过公共投资带动私人投资的增长。
2、参与东亚金融合作,保障我国金融安全经济全球化的金融全球化阶段,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的融合,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成为一种常态。因此,不同于布雷顿森林时代较为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必须面对充满风险的金融外部环境。这样,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即保证金融体系健康有序地运作,尽可能地减小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信心危机发生,从而实现对金融风险控制。理论与实践表明,金融合作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
金融安全不只意味着防范外部冲击,而且还要化解金融改革产生的累积风险,具有双重性。与之相适应,金融合作也不仅是单纯的走向单一货币同盟的模式,而是要同金融改革和规避金融全球化外部负面影响相联系起来。金融结构改革的表象是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对于自由化,其初期无序的经济环境和宏、微观政策改革几乎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导致理论上自由化带来的净经济福利水平难以实现。利率的放开、信贷指导政策的解除和银行进入壁垒的降低会导致金融机构隐性税收和相关租金减少,从而改变风险承担和激励机制,最终出现更大的短期经济波动和风险的累积。由此从金融压抑到自由化再到金融危机几乎成为金融结构改革的范式。
从目前的理论研究看,深化金融结构改革和打破“金融压抑——自由化——金融危机”的怪圈的方法是:第一,改变自由化的顺序;第二,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管手段、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重要的是,金融改革的同时要避免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建立审慎性的监管制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无疑能降低金融改革的风险,但建立与技术、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适应的制度性体系却需要长期的大量投入,这不是单个国家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实际上,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经济体没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来按部就班地实行自由化,现实情况是金融、财政、内部、外部改革同时进行、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早已同国外金融市场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就是过早过度的金融开放同内部改革滞后的矛盾结果。
综上论述,如果要在进行金融结构改革的同时实现不受外部冲击的经济增长,那么区域金融合作是理性且必要的一种选择。金融合作的作用主要有:在区域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建立屏障,为金融改革提供相对封闭的环境;综合利用区内的金融资源的规模优势和“同行监督”机制来推进制度改革的进程;共享金融结构改革的经验,降低制度改革的学习成本。
具体合作措施:[52]
——推进东亚金融合作框架的制度化过程,重视参与东北亚包括宏观政策协调、汇率合作的机制建设;
——倡导务实合作,加快东亚债券市场、东北亚开发银行和区域金融结构重组等领域的合作。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参见2002年墨西哥洛斯卡沃斯《APEC经济领导人宣言》。
[3]从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到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都强调通过市场竞争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目前大多数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都围绕此点展开,本文认为这只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础方面,属实体经济范畴。
[4][美]高柏:“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4期。
[5]Giovanni Arrigh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p.300.
[6]Karl Polanyi. 1957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7]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John Williamson针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归纳出十项政策要点:(1)财政纪律;(2)公共开支重点领域转向经济效益高、能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保健、教育和基础建设;(3)税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收基础);(4)利率自由化;(5)竞争性的汇率;(6)贸易自由化;(7)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自由化;(8)私有化;(9)取消管制(特制取消进出口壁垒;(10)确保产权。
[8]本部分论述参考了吴志鹏等“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9]刘均胜:《亚太地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分析》,博士论文(2003),第94—101页。
[10]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和维护应归结于霸权国家的作用,霸权国家的作用是杜绝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同时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参见Kindlberger, C., 1986, “The World in Depressi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r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考察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可以发现1870——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和1944——1976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迅速、金融危机较少、国际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可以称之为以英国为金融霸权的国际金本位制和以美国为金融霸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其余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金融危机相对频繁、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可以称之为金融霸权的非稳定时期。参见钟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4期。
[12]对于全球化,有学者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美洲(见李慎之:“开展全球化研究”,《世界知识》,1994年第2期),也有认为始于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大规模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还有认为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见李宗:“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世界经济》,1996年第11期)。相比之下,经济区域化的出现一般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一体化为标志。
[13]20世纪90年代,全球兴起区域一体化浪潮,截止到2002年底,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已经达到了250个。WTO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RTA,RTA成员间贸易占2001年全年贸易的43%。参见《东亚自由贸易区多方案选择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3年6月,第5页。
[14]开放的地区主义在APEC表现的最为突出,不但APEC内部取得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成果原则上适用于非成员,而且APEC要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做出贡献。参见张蕴岭主编:《走出危机的阴影: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新挑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5]新区域主义也是个存在分歧的概念,Hettne B.认为该概念描述了一个包括文化、安全、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在内的从“异质”到“同质”的过程,而C. Perroni等则认为该概念指小国对大国做出的单方面让步现象。参见Hettne B.: The N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U WIDER, Helsinki, 1994, p.8.C.Perroni, John Whalley,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 or Insuranc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3, No.1, 2000, pp.1-24.
[16]刘均胜:《次区域合作的能动关系》,载张蕴岭、赵江林主编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5月,第73—75页。
[17]Krugman将处于同一个大陆上的国家组成的FTA称之为自然的(natural)FTA,将处于不同大陆上的国家组成的FTA称之为非自然的(unnatural)FTA.详见“The Move Toward Free Trade Zones,” I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pp.7-42. 后来,还产生了超自然(super-natural)FTA的概念,它用来指在由于跨洲运输成本较低,而内倾向性较强的FTA所导致的福利减少现象。详见Jeffrey Frankel,Ernesto Stein,Shang-jin Wei:“Trade blocs and the Americas:The natural,the unnatural,and the super-natur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47(1995)61-95.
[18][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19]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2001年第2期 。
[20]ADB’s Annual Report 2001“Empowering Nations by Regional Cooperation” //http:www.adb.org
[21]发达国家参与合作主要是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双边和诸边谈判争取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上述观点参见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合作”,《世界经济》,2002年5期。
[22]Maurice Schiff,“Multilateral Trade Liberlization,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and the Choice of FTA versus Customs Unions,” NBER working paper.
[23]秦晓,凌晓东:“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1-2。
[24]刘均胜:《次区域合作的能动关系》,载张蕴岭、赵江林主编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5月,第95页。
[25]李向阳:“新区域主义与大国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7-8期。
[26]C.Fred.Bergsern, ”Fifty Years of Trade Policy: The Policy Lessons” The World Economy, Vol24.1.2001
[27][日]山泽逸平著:《亚洲太平洋经济论——21世纪APEC行动计划建议》,范建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28]克鲁格曼:“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令人不安的真相”,《流行的国际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9]张献著:《APEC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30]关志雄:“缺乏战略思考的日本对华政策——各政府部门间的意见分歧”,2002年11月。
[31][美]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指出:“中国是一个区域性强国,在全球起作用,从一个角度看它是站在世界事务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站在世界事务的中心。”参见《长城和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8页。
[32][俄]亚历山大·科克沙罗夫:“新石油时局”,俄罗斯《专家》周刊,2003年5月。
[3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
[34][美]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35]参见《参考资料》,2004年6月2日,第5页。
[36]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极大地促进了以钉住美元为主的东亚国家的出口,成为东亚奇迹的引擎,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贬值,则导致了以钉住美元为主的东亚国家出现巨额经常帐户赤字,为亚洲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见[美]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59页。
[37]Calvo and Reinhart,Fixing for Your Life, NBER Working Paper, No. 8006, Fear of Float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7993.
[38]Yung-Chul Park and Daekeun Park, Creating Regional Bond Markets in East Asia: Rationale and Strategy.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PECC Finance Forum, July 8-9,2003。
[39]Rorbert Mundell,Prospects for an Asian Currency area,special lecture at the conference on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China’s Economic Presence,”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May 27-29,2002。
[40]货币自由兑换条件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基础、完善的金融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41]吴敬琏:“当前经济过热主要是体制性问题“,中国财经网2004年6月16日。
[42]据报道,因预期人民币升值,近千亿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43]美国的大战略就是维护美国作为唯一的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中国对美国战略应建立在三个基点之上:一是认可美国的超强作用;二是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进行合作;三是提高自己的实力地位。这三点构成中美关系的稳定支架。参见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6—17页。
[44]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会东亚回到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中(见戴维·康2004)。其实,无论从现实的可能性和未来目标取向上,中国更希望出现一个和平、开放、繁荣的东亚地区,形成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45]徐小杰:《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46]第一圈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大陆,第二圈包括北美、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太平洋,分别被称为“内需求月型地带”和“外需求地块”。
[47]新能源安全概念内容是,能源安全可以通过市场力量来解决;能源安全同环境保护、运输线路等密切相关。参见刘均胜:“中国面临的能源供给与需求形势”,载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633页。
[48]庞中英:“地区化、地区性与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
[49]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最近由于日本政府的插手使中国同俄罗斯建立的石油管线的计划落空,形成“安—大”和“安—纳”方案之争。
[50]张蕴岭 周小兵主编:《东亚合作的进程与前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5月,第185—200页。